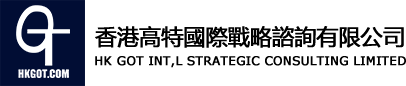美國該如何解決系統性警察暴力?
2020/6/18 18:01:44 Source:紐約時報中文網
全國示威活動已經持續數週,這樣的口號在美國各地的街頭迴盪,這明確了一件事:美國警察面臨著一場正當性危機。其後果遠遠超出警務本身。
決心重塑執法以糾正數十年種族不平等的人,不妨看看其他曾經努力應對這一挑戰的國家在這方面的經驗。堅持認為沒有問題需要解決的人也應該這樣做。
如今這個時刻植根於數百年的白人至上主義,又受到近年來瘋狂的政治兩極化的推動,從很多方面來說,它極具美國特色。但也有其他先例——幾乎全部來自那些系統性利用警察暴力執法維持少數特權階層權力的國家。
從美國街頭可以得出一個明顯的結論,美國的警察執法正在剝奪許多公民的權利,違背憲法承諾的依法平等保護。
美國警察暴力的嚴重程度;這種暴力被過多地用於黑人和其他受到嚴厲執法的少數族裔;不斷有犯錯的警察逍遙法外,令濫權制度化,所有這些都對美國民主構成了嚴峻挑戰。
「對這些社區來說,警察就是他們理解美國民主的方式,」研究美國警察執法和民主合法性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政治學家維斯拉·韋弗(Vesla Weaver)說,「他們確實從和警察打交道的經歷裡了解自己的民主公民身份穩固程度。」
儘管貧困社區首當其衝地受到警察暴力的衝擊,但美國各行各業的黑人都生活在警察暴力的陰影之下。
「在我位於坎布里奇的家中,就算沒警察,我腦子裡也會想到警察,」目前在華盛頓大學任訪問副教授梅根·明·弗朗西斯(Megan Ming Francis)說。
警察正當性危機並非美國獨有。北愛爾蘭、南非、斯里蘭卡和緬甸等地也發生過類似情況。儘管這些國家的一些經驗可能為美國如何著手解決當前動盪背後的問題提供指導,但它們也對美國所面臨挑戰的規模提出了嚴峻的警告。
「警察會很快失去正當性,」研究北愛爾蘭治安和政治的研究員克里斯托弗·裡卡德(Christopher Rickard)說。「要重新獲得它非常困難。」
「類似於專制的飛地」
直到最近,主流辯論還傾向於將警察殺人視為孤立事件,是個別警官的錯誤,或者「幾粒老鼠屎」的不當行為,而不是系統性問題的可預見後果。(愛說「幾粒老鼠屎」的人似乎忘了後面還有半句——「壞了一鍋粥」。)
但無論如何,這種區分可能是錯誤的。
在分裂的社會裡,如果對警察和其他安全部隊內部所謂的「老鼠屎」不加約束,「那不是能力問題,而是一種政治選擇,」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研究斯里蘭卡、緬甸和剛果民主共和國權力濫用行為的政治科學講師凱特·克羅寧-福爾曼(Kate Cronin-Furman)說。
「這樣做的目的是告訴邊緣化的少數群體,他們永遠都不安全,他們沒有充分的公民權利,他們的人性總是受到質疑,」克羅寧-福爾曼說。
這對佔主導地位的階級或群體提供了雙重保護:警察的暴力維護了他們在社會等級中的地位;而且掌權者通過默許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明確命令來鼓勵這種行為,從而可以合理地否認他們在暴行中所扮演的角色。
美國人並不習慣聽到自己的國家被拿來與克羅寧-福爾曼所研究的那些國家作對比。但有大量證據表明,縱觀美國歷史,暴力和壓迫性的警察執法向美國黑人和其他生活在貧窮、警力嚴密的社區內的少數族裔傳遞了類似的信息,而且這種情況今天還在繼續。
弗朗西斯研究過經政府認可的針對美國黑人的暴力行為,她說,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南方各州和城鎮的警務設計確保了剛獲得自由的黑人在經濟上仍處於從屬地位,在政治上仍被排除在公民權之外。
「他們把這些都寫下來了,所以他們想做什麼是很清楚的,」她說。「這被看做是剝奪那些新的公民權利的一種方式。」
其中許多成文法律最終都改變了,尤其是在南方的吉姆·克勞法(Jim Crow)時代結束後。但是,警察的暴力行為繼續向許多美國黑人傳遞這樣一個信息:他們不能充分擁有公民的權利和保護。
來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耶魯大學的研究團隊進行了一項名為「門廳警察執法項目」的研究,他們將海運集裝箱改裝為臨時會議場所,並將其安置在美國6個城市的12個警力嚴密的社區。每個集裝箱內都配備了通訊設備,這樣人們就可以和其他「門廳」的人討論自己的經歷,就好像他們共享一個空間。
在分析了三年來通過成千上萬次『門廳』對話收集的數據之後,研究人員發現美國人的生活圖景與克羅寧-福爾曼在亞洲和非洲觀察到情況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門廳』的參與者實際上是在講述一種類似於專制飛地的東西」,警察的做法剝奪了他們最寶貴的民權保護,該項目的主要研究人員之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的韋弗說。
研究人員發現,在一次又一次的談話中,人們列舉他們知道自己應該享有的那些權利,但隨後又說他們感覺到自己的這些權利被剝奪了。
他們擁有官方認可的隱私權,但警察可以在任何時候攔截他們,並對他們進行搜身。他們有官方認可的保持沉默的權利,但他們擔心如果不回答問題,警察會對他們進行騷擾或懲罰。他們有官方認可的和平集會的權利,但實際上,只要他們一起去公園的人數超過三個,警察就會以涉嫌犯罪活動為由給他們戴上手銬,拘捕他們。
「他們的經歷非常相似,都是極高的被遺棄感和被政府忽視的感覺,還有高度的監視,這些看起來都很像南方吉姆·克勞法的政治暴力,」她說。「這看起來非常像專制政權。」
錯誤的治安方法
隨著美國警務問題的嚴重程度得到越來越多的公眾關注,要求進行根本性變革的呼聲越來越高。明尼阿波利斯市上週投票決定完全廢除其警察部門,並用新警隊和新公共安全措施取代之。諸如「黑人的命也是命」之類的組織呼籲削減警察部門經費,並將其大部分職責重新分配。紐約和洛杉磯已經承諾從警察預算中削減掉數百萬美元。
來自其他國家的證據表明,即使有深化警察改革的政治命令,真正做出改變措施並不容易。
1994年南非第一次自由民主選舉戰勝了種族隔離政權時,新政府的諾言之一就是改革令人恐懼的種族隔離時代的警察。四年後,在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協議》標誌著四十年暴力宗派鬥爭的結束。它還承諾對警察進行審查和改革。
為了獲得正當性,南非和北愛爾蘭的警察必須超越其作為白人和新教政治主宰者的執行人的身份。這些努力的成敗取決於警察是否將繼續其過去的做法——把人們當作需要使用武力震懾管理的威脅,或者能否對平民的保護需求做出更迅速的反應,從而最終贏得全社會的信任。
牛津大學講師、研究南非警務和政治的講師喬尼·斯坦伯格(Jonny Steinberg)說,在南非,「警察保留了種族隔離時代的做法,即全副武裝的准軍事集團」。
他說:「當這種情況在壓制的政治情況下發生時,註定會造成極其不良的情緒。」隨著時間的流逝,中產階級和富裕的南非人轉而尋求私人保安,僱用警衛,搬到有圍牆的社區,乘私家車出行。而負擔不起這類措施的窮人則暴露於危險之中。
「這是美國的反面教材,」斯坦伯格說。「這是一個如何錯誤地對貧困的城市人口進行治安的標準範例。」
許多美國部門尚未吸取這個教訓。的確,近年來,准軍事戰術——通常包含通過政府的冗餘軍用物資計劃獲得的軍事裝備——在美國越來越受歡迎。
研究政策和政府合法性的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湯姆·泰勒(Tom Tyler)說:「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美國警察以威脅性的方式執行任務。」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他們都樹立了一個使用武力對抗危險人群的戰士形象,而不是社區的守衛者。
上週,紐約市最大的警察工會的領導人埃德·穆林斯(Ed Mullins)在給官員的信中,戰爭和威脅的措辭得到了顯著體現。「我們將在紐約市贏得這場戰爭,」他寫道。「這是正義對抗邪惡,而邪不勝正。」
相比之下,在北愛爾蘭,警察的確改變了他們在北愛爾蘭問題中使用的許多更為軍事化的平叛手段。但即使在和平協定簽署二十多年後的今天,研究員裡卡德說,警方仍經常難以說服受害者相信正式的司法系統,而不是轉向宗派准軍事團體提供的暴力正義。
「這在北愛爾蘭都如此困難,」他說。「我甚至無法想像要解決美國的這些結構性問題該從哪開始。」
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的政治學家卡尼莎·龐德(Kanisha Bond)研究「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以及其他旨在進行社會變革的黑人運動。她說,這些深層次問題解決起來勢必很困難。
「通過當代的行為,歷史被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她說。「你會看到抗議者、示威者和起義者直指核心問題,在他們看來這是一種系統性的解決方案。而且這肯定是令人不舒服的。」